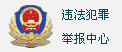○劉琴琴
韓嘉川的散文詩《堆滿倉(外四章)》,構建了一個兼具歷史厚度與抒情張力的文學空間。作者通過對記憶的文學編碼、歷史記憶的在場性重構以及抒情主體的間性建構,使之呈現出獨特的詩學品格。
記憶的文學編碼
韓嘉川擅長將抽象的歷史記憶轉化為可感知的物質意象,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符號系統。在《堆滿倉》中,“獨輪車轍痕”與“倒春寒里的野菜”構成物質符號的雙重指向:前者承載著農耕文明的集體勞作記憶,后者則暗喻饑荒年代的生存經驗。詩人通過“大地就是糧倉/只是過于輕信”的復沓修辭,使自然意象在重復中發生語義增殖——從一開始對土地的質樸信任,逐漸演變為對歷史創傷的隱晦指涉。這種寫作策略避免了歷史書寫的直白化,讓讀者在詩意的表達中也能感知歷史的隱痛。
《長衫先生》則通過聚焦“寶藍色長衫”等細節,形成了對民國知識分子精神的物質錨定。長衫“雙肩發白”的磨損痕跡,既暗示時間流逝,又隱喻文化傳承的艱辛。當詩人將聞一多的詩句“銅的要綠成翡翠”與“撿拾柴草的孩子”并置時,通過物質景觀的對比,揭示了啟蒙理想與現實困境的永恒張力。這種將理性思辨視覺化的處理方式,使抽象的歷史命題獲得具象的審美載體。
歷史記憶的在場性重構
韓嘉川打破線性史觀,通過時空折疊創造歷史的多聲部對話。《浣花溪》中,“少女的鏡頭”與“晚唐茅屋”形成時空蒙太奇,數碼時代的觀看方式與古典詩意產生奇異共振。詩人以“麻雀承當省略號”的意象,喻指歷史敘事中的斷裂與空缺,而“折斷的桂花映照聽秋人”則通過物象的瞬時接觸,搭建起跨越千年的審美通感。這種敘事方式消解了歷史與當下的二元對立,使不同時代的文化記憶在詩意空間中共存。
而《青州光陰》對李清照的追慕,則展現了“以空間寫時間”的獨特路徑。詩人避開生平考證的窠臼,轉而通過紀念祠的空間體驗——“鏤空閑窗透風聲”“銷魂暗香寄存葉瓣”——將詞人的文學氣質轉化為可觸知的具象物境與空間氛圍。當“北宋石板路”與“當代訪客”在詩中相遇,物理空間成為連接古今的情感媒介,實現了歷史記憶的在場性重構。
抒情主體的間性建構
韓嘉川在作品中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抒情主體位置——既是歷史觀察者,又是記憶參與者。在《浣花溪》中,“少女用鏡頭捕捉茅屋上的風”與“戴葦笠的老翁已退遠為背景”形成了時空并置的視覺效果,抒情主體在這種并置中獲得了穿越時空的觀察視角。這種主體位置既保持了適當的審美距離,又包含著深刻的情感投入。
《青州光陰》中抒情主體的建構更為復雜。詩人以“在北宋的石板路上,不敢翻動風的走向”的謹慎姿態,展現了對歷史記憶的敬畏之心。這里的抒情主體既是當代訪客,又通過“藕花索引無數尋尋覓覓的目光”等意象,與李清照的文學世界建立了精神聯系。這種間性主體位置,避免了簡單的歷史代入或冷漠的客觀描述,創造了一種既親密又克制的抒情姿態。
韓嘉川以物的詩學對抗宏大敘事,用微觀視角解構歷史整體性,在記憶的褶皺中開掘出豐富的意義層次。其語言既保有散文的敘事肌理,又充滿詩歌的意象密度,在“及物”與“超越”之間形成獨特張力。這種歷史記憶的文學重構,本質是通過審美形式對時間進行再編碼。當“堆滿倉”的民謠在詩中回響,當寶藍長衫在海風中飄動,韓嘉川確證了散文詩作為歷史想象載體的可能性——它不僅是記憶的容器,更是意義的生成場域,在語言的煉金術中,將過往轉化為持續作用于當下的精神力量,這就是散文詩的記憶詩學。






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
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